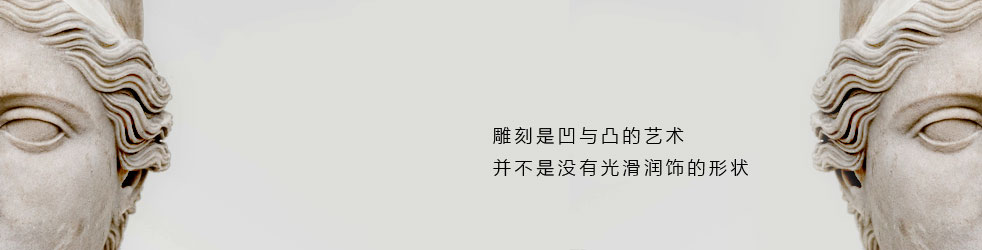
回忆与抵达—读刘若望雕塑作品
在文化资本透支的当下,回忆本身就是一种昂贵的奢侈。奇货可居的市场运作,也使回忆变为商品。在虚构的历史语境中,微缈的视角更是被贴以个性的标签。关注恒定而永久的精神维度,不啻于思想的冒险。因为,那很容易被资本权贵以金钱的天枰加以衡量,一旦失去媒体或所谓“主流话语”的聚焦,就以藐视的目光将其打入观察的暗角。 从这一点来看,刘若望的回忆与坚守近乎执扭。对投机者而言,民族的灿烂过于耀眼,不如躲入松荫,把酒欢盏,让沉重在无聊与虚无中消解。虚拟的图像,伪造的困窘大都描画着未来的极乐世界,以此来建立中国人已在审美上进入了后现代的进步体系的信心。回忆过去,也应当站在西方“他者”的视角来涂抹,伪造的民俗和色彩最可能轻松入围,太宏大而真挚的创造容易戳破假面,长袖善舞也自然会被揭去肤浅的表皮,从这一点看,刘若望的艺术“不合时宜”。 然而,刘若望创作的珍贵却又在于此。他出生于古老的三秦大地,残破的瓦当与兵马俑,使贫瘠的土地具有了历史的充沛营养,那是尚未发蒙就已开始吸吮的乳汁。同时,革命老区的特殊身份,也使这片土地涌现过无数的传奇和激情。大同社会和善良的祈愿是支撑秦腔的一口底气,那意味在他们忠厚的表情背后是无法言语的慷慨激昂。这些共同构成了刘若望艺术的根脉。 当他游走在西方艺术的技法长廊时,回忆似乎是内心呼唤着的号角,使他无法不驻足回眸。在他的作品中,民族的精神与其说是造型的表达,不如说是灵魂的一缕挂牵。看《东方红》,如看秦俑,通过无数均质的个体重复,产生排山倒海的力量,他们在为寻觅幸福而长久呐喊。观《人民系列雕塑》,却如读加缪,纯朴的人以西西弗般的执着将历史的巨石推倒高点,具有调侃和反讽意味的却是,他们仍然生活在贫困与期待中,真可谓近乎宿命的悲剧。 而这种抵达元素的力度,不免让人被刘若望的思考维度所震动,毕竟,他刚及而立之年,这是都市男孩的消遣岁月,是花前月下的轻柔与曼妙,刘若望却以回忆的方式使自己的艺术浸透了三千年的文化血脉,这是何等的严肃与沉重。也许,回忆并不是唤醒一个时间,实际上是建构让魂魄回家休憩的场域,在那里最重要的不是对抗虚伪民俗的矫饰,而是让纯粹的记忆阻止尴尬的忘却! 韩雪岩 丁亥年二月二于清华园曦和斋
发表评论
请登录